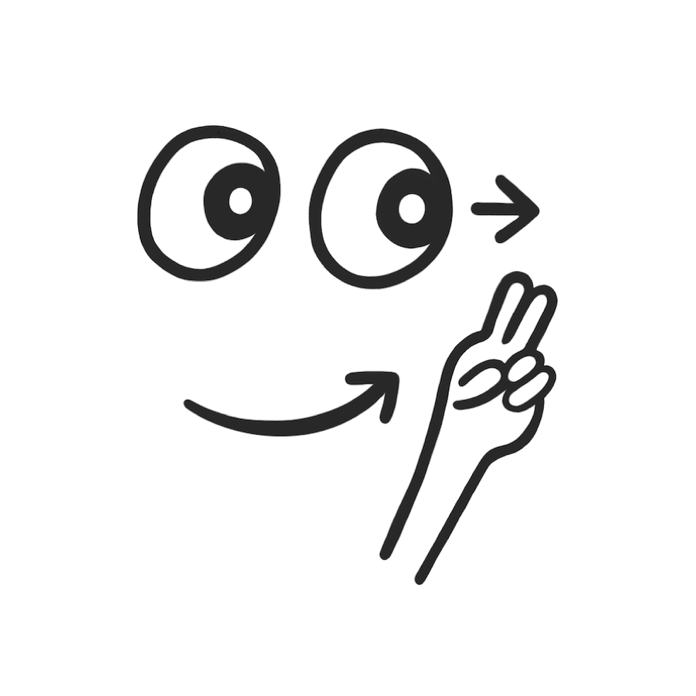一覺起來就「開悟」?馬哈希|拜倫 凱蒂|當下的力量、托勒
有位讀者跟我分享了他經歷了一段非常獨特的經驗。折騰他多年的雙向情緒障礙,忽然在某個夜晚全消失了,他問我說這是不是「開悟」經驗。
我知道這不是開悟,但我很好奇這是什麼現象,不了解,多年困擾他的情緒障礙,為什麼一夜間消失了?所以我們簡單聊了一下。這一聊,徹底解開了一個困惑我很多年的疑問。
讀者說,他說自己有10多年的抑郁史,2年前在医院診斷为双向情感障碍。他說药物可以帮助他睡眠。過程中,他也读了很多书,發現自己雖然懂道理,但是内心怎么也走不出来,很多的努力,但是都仍然无法消除他内心的情绪。
半年前,有一次「由于睡觉时呼吸暂停,体验了一次濒死,醒来后脑中的声音消失了,让人痛苦的情绪也消失了。这种状态从去年12月持续至今。除了有一次2月份重感冒时暂时脱离这种状态。」
非常類似其他 3 個案例:
《當下的力量》的作者 Eckhart Tolle
提倡「自我詢問」self-inquiry 的 Ramana Maharshi
《一念之轉》四句話的 Byron Katie。
Eckhart Tolle,長期重度憂鬱,經歷一次極度的內在痛苦後,有天深夜,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恐懼,不斷問我是誰,這念頭是誰的,忽然間,他說那個一直令我痛苦的『我』,突然崩解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平靜與覺知。
Ramana Maharshi,青少年時,一個突如其來地體驗到強烈的「死亡感」,強烈的恐懼,彷彿自己就要死去,他專注觀察:「誰是這個要死的我?」 在這番探問中,強力的恐懼感忽然消失了,而感受到一種深沉的寧靜與不動的覺知狀態。
好比 Byron Katie 曾陷入嚴重的憂鬱症、焦慮、酗酒與暴食困境,甚至無法離開家。但某一天早晨,她在康復中心的地板上醒來,突然經歷了一種「覺醒」,她意識到「痛苦並非來自事情本身,而是我們對事情的信念。」改變了她看待人生的方式。
對比這些案例,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特性,就是:他們過去多年被某些心理狀況所困擾,無論是雙向、抑鬱症、或極端恐懼,努力想要克服,但走不出來,但到了某個臨界質 → 產生靈性經驗和療癒效果 → 抽離自我 → 困擾他們很多年的情緒問題,忽然一夜間都消失了。
我之前想不通為什麼,但讀者提醒了我一點,他猜測「有一种说法是濒死經驗,让松果体分泌DMT,治愈了情绪问题。」
我突然恍然大悟,啊,對的,就是這原因!
DMT 這種化學分子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,但大腦自己也可以分泌一定的量,雖然通常很少。DMT 又被稱為 The Spirit Molecule,靈性分子,因為它可以誘發靈性經驗。
DMT 是 psychedelics 的其中一種。如果你翻閱美國頂尖學術機構的臨床心理研究報告,哈佛、Johns Hopkins、UC Berkeley⋯⋯你就發現很多人都分享著類似的經驗。Psychedelics 往往會誘發「靈性體驗」,同時,產生潛在的療癒效果。但需要提醒的是, psychedelics 在多數地區仍屬違禁藥物。
臨床報告顯示,許多人形容不只是困擾自己的情緒,也許是抑鬱、創傷的恐懼、成癮,減弱了,甚至消失了,更是經歷了一種深層的生命領悟。「焦慮就像一場夢一樣散開了,剩下的是純粹的存在。」對於瀕臨死亡的重症患者,「我看見死亡不再是終點,而是一種自然的回歸。在那一刻,我放下了恐懼,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安詳。」
產生「靈性體驗」並不容易,但如果進入深度的冥想、深度的催眠,或是臨床時使用 psychedelics,都可以讓大腦進入「意識改變狀態」(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)。產生一些很特別的體驗,好比「自我解體」(ego dissolution)或「無我」(no-self)。
簡單來說,你會感覺到所有佛陀、老子、高僧、身心靈導師,所感受到的那些深刻體悟。所以同時,你也會領悟到「靈性體驗」不是,也不等於「開悟」。
腦神經科學研究發現,這類現象與大腦的運作有關。好比大腦中有一個叫做「默認模式網絡」(Default Mode Network,簡稱 DMN)的系統。DMN 負責「自我意識」、內在對話、自我參照的思考、反思過去、擔憂未來。當 DMN 腦部區域活動較強時,你會感到很多思緒、自我感鮮明,但 DMN 活動減弱時,「自我中心」就會安靜下來,你就會體驗到「自我解體」、「自我消融」、無分別、一體性、無我等感受。
「靈性體驗」往往伴隨著療癒的效果。或是準確的說,深度的意識改變狀態,產生了靈性經驗,同時,也產生了療癒效果。
你可以理解,當一個人困在某個情緒裡走不出來,困在焦慮或抑鬱中,並不是我們真的想要困在那裡,但大腦就是跳不出特定的神經元迴路,一直在那兜圈子,一直焦慮,一直抑鬱。一個人感情分手,他很抑鬱,他很痛苦,卻又很難從那種痛苦的情感中走出來,並不是說我們想要。
所以如果讓大腦進入「意識改變狀態」,類似深度冥想或催眠的意識狀態,大腦可以產生更高的思維彈性,有機會跳出原本僵化的神經元迴路,重新開展新的神經連結。原本腦袋神經元打結,現在解開了,原本打死結的情緒就自然消失了。
在被譽為「美國心理學之父」威廉・詹姆斯(William James)的心理學與宗教研究的里程碑著作《宗教經驗之種種》(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) 中,也提到了一些類似的現象。
在一位18世紀的傳教士 Henry Alline 的自傳中,描述了自己年輕時陷入的極度絕望,生命被罪惡的念頭所折磨,在恐懼中的掙扎。對自己感到無比厭惡,同時又對上帝的律法感到恐懼。
「我所見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我的重擔;大地彷彿因我而被詛咒:所有的樹木、植物、岩石、山丘與山谷,都像披上喪服,呻吟於詛咒的重壓之下,萬物似乎都在合謀要毀滅我。
我的罪惡像被攤在眾目之前,我甚至以為每個人都知道;有時我幾乎想承認許多我以為他們已看透的事。是的,有時我彷彿看見所有人都指著我,視我為世上罪孽最深的可憐人。
我此刻深切感到世間萬物的空虛與貧乏,知道整個世界都無法使我愉快,甚至整個受造界也做不到。清晨醒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:『噢,可憐的靈魂,我該怎麼辦?我要去哪裡?』夜晚躺下時又想:『也許天亮以前我就會墮入地獄。』
我常滿懷羨慕地看著牲畜,多麼希望自己能在牠們的位置,那樣我就沒有靈魂可以失去。當我看到鳥兒飛過頭頂,常在心裡想:『啊,要是我能像牠們一樣飛離危險與苦難該多好!要是我能在牠們的位置上,我該是多麼幸福!』」
Alline 長期備受精神折磨,處於絕望之境,但有一天他經歷了神秘體驗,感覺自己被一道神聖之光所包圍,瞬間充滿一種無法言喻的喜悅與確信。幾分鐘前還在痛苦掙扎,現在卻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愛與喜悅。
「傍晚接近日落時,我獨自在田間走著,一邊為自己悲慘、迷失、無可救藥的處境哀嘆——沉重得快要壓垮我。我甚至覺得:從來沒有人像我這麼慘。我回到家門口,正要跨過門檻時,心裡忽然響起一個細微卻極有力量的聲音:『你一直在尋求、禱告、改過自新、勞苦、讀書、聽道、默想——這些對你的得救有什麼用?你現在比剛開始時更接近「歸信」了嗎?你更預備好上天堂、或站在上帝公正審判台前了嗎?』
這些話重重打在我心上,我不得不承認:我一點也沒有比當初更接近救恩。我依舊被定罪、依舊暴露在危險中,仍然和以前一樣痛苦。我在心裡呼喊:『主啊!我的上帝,我迷失了!如果祢不為我開出一條我從未想過的新路,我就永遠不得救。我自己想出的那些方法全都失敗——我願意承認它們失敗。主啊,憐憫我!主啊,憐憫我!』
這些異象一路伴隨我,直到我進屋坐下。剛坐定,心中一片混亂,像將溺水的人拼命掙扎⋯⋯當我把一切全然交託,讓神自由掌權時,救贖的愛攜帶經文衝入心中。罪咎重擔瞬間脫落,黑暗被驅散,內心謙卑且滿溢感恩。剛才還在死亡山嶺下呻吟的我,如今被不朽的愛充滿,信心展翼高飛,高呼:『我的主、我的神!祢是我的磐石、保障、盾牌與高臺,是我現今且永遠的喜樂!』
我抬頭,又見那道熟悉卻更明亮的光。光一顯現,神的旨意隨即敞開⋯⋯瞬間,靈魂在神裡甦醒,被永恆之愛擁抱。黎明時分,我喜悅地起床,並告訴我的父母關於上帝對我靈魂做的事,翻開《聖經》要示經文,整本書對我而言是全然新鮮。此後,我只渴望成為基督的器皿,迫不及待要向世人講述救贖之愛。我對世俗享樂與應酬全無興趣,也蒙恩得以遠離它們。」
這看似「上帝」的示現,但並沒有一個個體的存在,所以大概是靈性經驗的體悟,過去的痛苦忽然煙消雲散。這類案例其實並不罕見,也可以在瀕死經驗的案例中發現類似的現象。
回到上述案例中,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共性,他們都不是在清醒的意識狀態中「想通」的,而是在頻死經驗、躺在床上、地上,進入意識改變狀態時,鬆解開困擾他們多年的情緒。
讀者說
「现在回头看这些书,就跟各种药一样,治病的原理都懂,要吃到身体内,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。感悟、感觉是非语言的,只有内心体验过了,才能达到这种境界。」
冥想可以進入意識改變狀態,但除非長期練習,不然很難走入深層的意識狀態,所以我們鼓勵大家透過眼動的方式,進入意識改變狀態,來鬆解情緒,跳出過去的思維慣性。